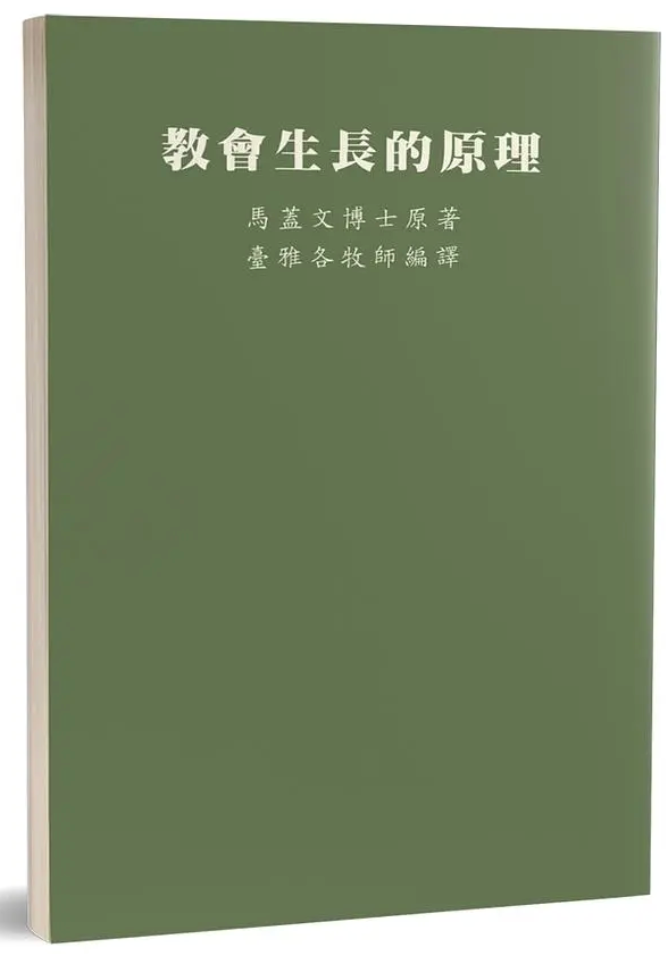
马盖文(Donald A. McGavran),《教会生长的原理》(Understanding Church Growth),Grand Rapids:Wm. B. Eerdmans 出版社,1990 年。332 页。中译本由橄榄华宣出版。
在中东晨跑时,我常看见当地人沿着海岸抛竿垂钓,耐心等候鱼儿上钩。有些渔夫似乎比别人更容易满载而归。我常想象这些早起的能手,带着鱼回到家中时,家人一定欢欣迎接。
然而,有一天我与一位当地人同跑时,我的看法改变了。他告诉我,海洋研究人员曾警告居民不要食用海湾里的鱼类——因为水中含有大量金属物质,食用这些鱼对人身体有害。渔夫们虽然能把鱼带回家养家糊口,但他们真的该这样做吗?
类似的问题同样适用于马盖文的著作《教会生长的原理》一书。这本书详细阐述了教会增长的运作机制,这的确可能带来增长。但问题是:今天的牧师和宣教士是否应该照搬这种方法?马盖文的方法论真的安全吗?
马盖文痛心指出,二十世纪中后期的教会偏离了核心使命,陷入“普遍迷雾”中(55 页)。他写道:“宣教的首要且不可替代的目标是教会增长。社会服务固然蒙神悦纳,但绝不能取代寻找失丧灵魂的使命”(22 页)。他热切呼吁教会重新聚焦在增长上:
大型布道运动刻不容缓,这是福音前进的途径之一。但正如本书清楚展示的,布道运动必须以这样的方式进行:能建立众多新的教会,使许多新信徒成为基督身体里忠心可靠的肢体。”(xvii–xviii)
今天我们很容易对马盖文的忧虑感同身受。在许多教会中社会关怀仍然挤占了福音事工的位置。对此,我完全认同马盖文的提醒:我们必须殷勤去寻找失丧的人,向他们传讲福音。然而,我不同意他所提出的具体做法。
在说明理由之前,我们需要先明白,这本书至今仍具深远影响。
马盖文的思想,尤其是他强调社会科学对教会增长的价值,在 20 世纪 70 年代广受认可。拉尔夫·温特(Ralph Winter)的著作也在同一时期问世,他将宣教目标重新聚焦于“未得之民”。
温特的民族志(ethnographic,是一种写作文本,它运用田野调查来提供对人类社会的描述研究。——译注)视角帮助重新定义了宣教对象,而马盖文的社会学方法则提供了触达这些族群的工具。过去难以想象的规模,如今似乎近在眼前。马盖文主张的一项策略,是不要在新信徒归信后立即将他们“拔离”原有的社会关系,而是把他们视为“桥梁”,藉此影响他们的整个社群。他指出,外国宣教士往往因为“人们更愿意在不跨越种族、语言或阶级壁垒的情况下成为基督徒”,反而筑起了不必要的社会障碍。
这一理念后来被称为“同质单位原则”(homogeneous unit principle),旨在纠正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殖民色彩浓厚的宣教模式(163 页)。马盖文详细记载了“群体归信”(people movements)的现象——在本土文化内部,大批人同时归信基督。于是,宣教学界开始畅想新的增长可能性。温特帮助聚焦宣教目标,马盖文则点燃了对大丰收的期待。《理解教会增长》一书也因此吸引了广泛读者,自1970 年起的二十年间三度再版。
直到今天,马盖文的方法仍深深影响着许多宣教策略家,尽管很多人未必熟悉他的名字。在本土化方法的极端实践中,所谓的“局内人运动”(insider movements)鼓励新信徒继续保留在原有宗教社群中,以期发挥更大影响。这种思路可以追溯到马盖文的“上帝之桥”(bridges of God)理论和“家庭网络”增长模式,其中寻找“平安之子”是关键。支持这种做法的根据常见于《马太福音》第 10 章等经文,但其背后依然延续了马盖文的“同质单位原则”。
即便在非宣教语境中,马盖文的影响依然显而易见。西方的“吸引式事工”往往围绕年龄、阶段、兴趣等自然的亲和力来发展小组。其逻辑与马盖文的方法一脉相承:只要减少社会学层面的阻力,教会、运动或小组自然会增长。毕竟,物以类聚,这理应成为增长的有效途径。
回到捕鱼的比喻,现代的事工蓝海中几乎处处弥漫着马盖文的影响。我们在不知不觉间,把他的社会学理论视为教会增长的关键。
但问题是:在这样的水域捕鱼真的安全吗?只要教会增长,就不会出错吗?
在这片水域里,有两种“外来元素”使这种增长弊大于利:
对马盖文来说,圣经的权威已经被结果取代,而他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他写道:“教会增长源于合乎圣经的神学与忠心。它大量借鉴社会科学,因其始终发生在社会之中。它不断追寻上帝赐下增长的实例,然后追问:究竟哪些因素蒙祂祝福,从而带来如此的增长?”(xiv页)
请注意马盖文如何把“忠心”与“结果”紧紧捆绑:忠心因带来增长而被肯定。毕竟,神不喜悦“徒具形式的追求”,即看不见果效的努力(6 页)。换言之,凡能带来增长的因素,就是蒙神认可的“正确因素”(132 页)。这种逻辑在当代教会增长论者那里常被包装为一句俗语:“疯狂就是重复做同样的事却期待不同的结果。”这也是为什么他的书中充斥着案例研究——以可见的果效来论证“目的正当化手段”。他甚至说:“教会增长就是忠心”(6 页)。这正是典型的实用主义。
请别误会:我们都渴望果效。但这里张力在于方法,例如所谓的“真实因素”——既可能确保收成,也可能腐蚀收成。这正是其中的危险所在。
公平地说,马盖文在书中偶尔也会提醒读者不要过分依赖方法。但从整体来看,他的书仍在高举方法论。他说:“缓慢的进展本身既非圣经教导,也非属灵表现。有时必须忍受,但没有理由将其奉为圭臬”(121 页)。然而,讽刺的是,他整本书却在高举那些能迅速产生果效的方法。他劝人不要神化方法,但他却用“神的印证”作为方法合理性的证明。
马盖文对《使徒行传》的解读中,“神化”那些立竿见影的方法的倾向十分明显。《使徒行传》叙述了早期教会在犹太人中扩展的过程,但可悲的是,随着外邦教会的兴盛,犹太人的抵制却日益加剧。马盖文把责任归咎于哪里?真正阻碍增长的因素又是什么?
然而,当大批外邦人成为基督徒后,对犹太人而言,作基督徒往往意味着离开犹太民族,融入一个由多元群体组成的社会。接纳外邦人反而形成了种族壁垒。合理的推测是:当作为基督徒意味着要加入充满外邦人的家庭教会,并参与“爱筵”(甚至偶尔会有猪肉上桌)时,潜在的犹太信徒因种族和文化隔阂过大而痛心离去。从那以后,犹太人普遍拒绝福音(169–170 页)。
换句话说,耶路撒冷会议错失了“社会学的机遇”。他们的认知盲区导致错过了犹太人信主的“潜在收割”,并为近两千年的抗拒埋下了祸根。马盖文哀叹这是一场收割的悲剧,而不是颂扬一间多元教会中神恩典的胜利。
如果社会学的壁垒真是犹太人抗拒的主要原因,那么《使徒行传》前几章中犹太人归信的真正因素是什么呢?在马盖文看来,彼得似乎正好应用了这种“社会学秘诀”:
教会赢得了那些可赢之人——趁他们还可以被赢得之时。倘若五旬节那天彼得为了赢得外邦人,就要求所有潜在的归信者在饮食、婚姻、敬拜和传道上都实行包容,而使徒们也立刻像对待犹太人一样,把同等的精力放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地的外邦人身上,那么最终成为基督徒的犹太人将屈指可数。(29 页)
你看出这个逻辑了吗?五旬节就这样被解读成古代社会学的兴起与胜利。在马盖文的视角里,“同质性”带来了犹太人的丰收,而“异质性”(heterogeneity)则阻碍了《使徒行传》15 章耶路撒冷会议后的收割。圣灵所成就、原本超越人力的神迹,竟然被社会学的规律所取代。
这正是水源受到污染之处。马盖文的释经始终被他对“成果”和“同质性”的先入立场所支配。这让我担忧:他并不是顺服圣经本身的教导,而是利用圣经来强化一种实用主义、受社会学驱动的教会增长模式。
然而,圣经早已指出:当福音的种子落在刚硬的心田时,即便是忠心的传道人,也会遇见没有果效的听众。这才是保罗对犹太人抵挡福音的解释。他对听众说:
圣灵藉先知以赛亚对你们的祖先所说的话是不错的。他说:
“你去告诉这百姓说,
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
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
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
耳朵发沉,
眼睛闭着;
恐怕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
心里明白,回转过来,
我就医治他们。” (徒 28:25-27)
我们对神的心才是症结所在,而“同质性”并不是脱离罪恶的救主。
无论是保罗,还是耶稣在“撒种的比喻”中,都没有把没有果效归咎于缺乏信心(可 4:1–20);他们也从未把丰硕的果效归功于同质性(太 16:17;林后 4:6)。
同质群体中也许会有增长,但如果这种增长必须依赖同质性,那么自然的手段就取代了超自然的作为。一个因同质性而被接受的“福音”,不会使人真正拥抱多样性。马盖文虽期待教会最终成熟为多元且合一,却未察觉:那本应打破社会隔阂的福音,已被人挟持。最终,这些毒素会摧毁我们真正渴望的成长。
这并不是哀叹福音在大学生、年轻夫妇或偏远岛屿未得之民等同质群体中的果效。我的忧虑在于马盖文的预设:所有增长都等同于忠心,而同质性是开启增长的关键。对他而言,“不阻碍圣灵、不限制教会增长的正确方法”就具有权威性(142 页)。方法已经取代了神迹。正因如此,他最终误解了真正的教会增长,把可见的果效与圣经所说的忠心混为一谈。
这也不是说马盖文的观察对读者全无益处。但读者必须谨慎,就像中东的渔夫一样:外来元素已经渗入港湾,这片水域终究是不安全的。
译:DeepL/STH;校:JFX。原文刊载于九标志英文网站:Is All Church Growth Good Fru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