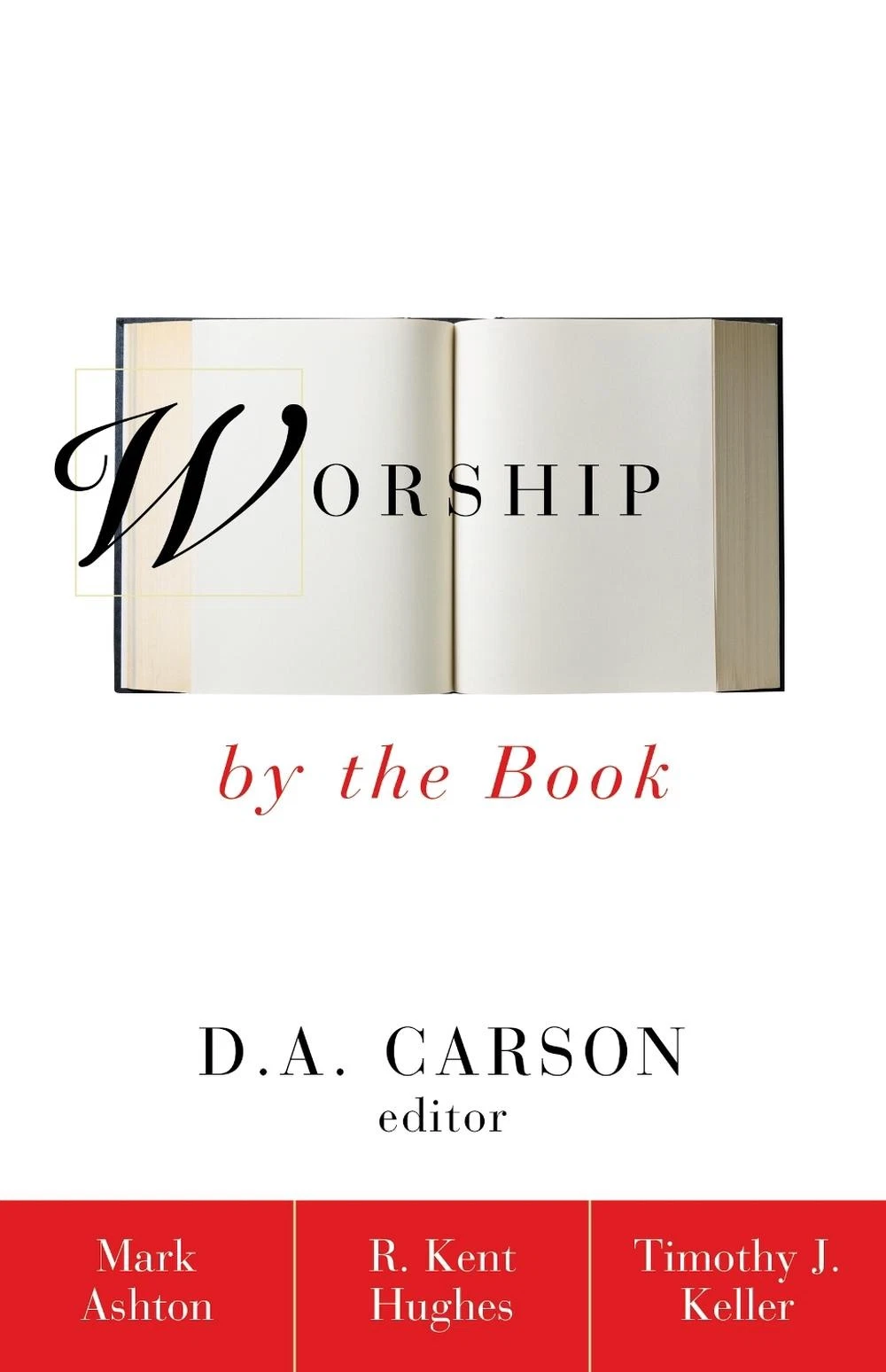
近年来,太多教会因所谓的“敬拜之争”而支离破碎。坦白说,我对“敬拜之争”这一说法始终感到别扭。创造这个词的人,要么完全忽视了“敬拜”一词的真正含义,要么就是极其敏锐地捕捉到了教会生活中一种令人哀叹的讽刺现象。我更倾向于后者。然而,如今这个词得到如此随意地使用——甚至常常伴随着轻松的幽默和会心的微笑——我不禁怀疑,还有多少人仍能意识到这两个词并置在一起时所产生的强烈张力。若说什么时候神的子民最应当彼此合一、并与他们的主同心,那必然是在一同参与共同敬拜的时候。但不知何故,共同敬拜竟成了一件充满争议、引发分裂的事,以至于我们不得不用“战争”这样沉重的词来形容它。
这些纷争中,至少有一部分无疑要归咎于牧者——他们竟容许“音乐风格”成为共同敬拜中至高无上的议题。距离宗教改革已过去四百多年,如今再去讨论共同敬拜应当如何进行、以及这些问题为何重要,似乎显得近乎迂腐。为什么要花时间思考,认罪是否该接在经文诵读之后,或反过来?
《按着圣经敬拜》正是四位作者联手作出的回应,试图把这些问题重新带回我们的视野,再次教导牧者如何以谨慎而合乎神学的方式来思考共同敬拜。本书由唐·卡森(Don Carson)、马克·阿什顿(Mark Ashton)、肯特·休斯(Kent Hughes)和提摩太·凯勒(Tim Keller)各撰写一章。阿什顿、休斯和凯勒三位都是牧者,分别来自圣公会、自由教会(指独立教会,不是自由派的意思——译注)和长老会传统,但他们同样坚定地委身于上帝话语在共同敬拜中的权威与中心地位。第四位作者卡森则是伊利诺伊州三一福音神学院的教授。四位作者在某些其他观点上并不完全一致,但若将这些专文合在一起,它们构成了一次极其宝贵的“重新推介”,引导我们不再以实用主义,而是以圣经和神学的方式,重新思考什么是共同敬拜。
卡森的专文“圣经话语下的敬拜”("Worship Under the Word")奠定了本书所有作者所共享的神学框架。仅就其广度与基础性而言,这篇专文便是全书中最具价值的一篇。全文长达 52 页,以极其谨慎、严密且彻底以圣经为根基的方式,论述敬拜这一主题。卡森先指出敬拜之所以难以讨论的多重原因,继而给出一个相当详尽的敬拜定义,最后围绕该定义提出十二个论点,并逐一加以阐述。这些论点对任何认真思考敬拜问题的牧者而言,都极其有益。
卡森一贯以细致入微的严谨态度和独到的视角展开写作;在我看来,这正是他区别于当今其他福音派思想家的地方。一位朋友曾打趣说:“当你遇到问题时,先把所有相关资料都读一遍,自己好好想一想;然后再去读卡森——那感觉就像翻到书后的答案页。”卡森的这篇专文从多个层面为讨论带来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视角。首先,他对圣经整体叙事——救赎历史的推进,以及神向其子民启示的渐进性——有着深刻而自觉的把握,并且在论述中切实加以运用。这使他能够避免一种常见陷阱:直接从旧约中寻找依据,以此为今日的敬拜实践辩护。正如他所说:
若我们不加分辨地使用整本圣经来建构我们的敬拜神学,便可能陷入一种任意而主观的用法。例如,我们注意到圣殿事奉发展出了诗班,于是便断定我们的共同敬拜也必须有诗班。也许确实如此——但在这一推论过程中,我们并未认真思考圣经整体是如何彼此连贯的。我们今日并不存在旧约意义上的“圣殿”。那么,我们究竟凭什么把旧约的诗班移植到新约,却舍弃旧约的圣殿或祭司制度呢?(17 页)
除了其救赎历史的视角之外,卡森也谨慎处理了“全人敬拜”(all-of-life worship)与共同敬拜之间的区分。若基督的降临使一切空间、时间与饮食都被“重新圣化”(re-sacralization),那么基督徒又如何理解:教会的共同聚会在某种特殊意义上仍然可以被称为“敬拜”呢?对这一问题的把握——也是本书所有作者共同的出发点——揭示了使用诸如“敬拜中心”或“敬拜领袖”等说法的怪异之处,尤其当后者实际上把敬拜等同并局限为唱诗时。卡森指出,在新约之下,整个基督徒生活都属于敬拜;与此同时,教会的共同聚会同样也是敬拜。他这样解释到:
换言之,敬拜成为我们安排生命中一切事物的总范畴。无论我们做什么——即便只是吃喝;无论我们说什么——无论是在职场、家庭,还是在教会的聚会中——我们都当为神的荣耀而行。这就是敬拜。而当我们一同聚集时,我们便是以群体的方式参与敬拜。(46 页)
最后,卡森的这篇文章还穿插着大量实践性强、洞见深刻、甚至颇具幽默的建议;在此不再逐一转述,以免剥夺读者亲自阅读与体会的乐趣。
马克·阿什顿是英国剑桥圣安德烈大教堂圆形教堂(Round Church at St. Andrew the Great)的牧师。他的专文“追随克莱默的脚步”("Following in Cranmer's Footsteps")这一标题可谓恰如其分。阿什顿以托马斯·克莱默(Thomas Cranmer)的《公祷书》为起点,感叹英国圣公会中有许多人“花了太多时间赞叹其中优美的语言”,却“对其属灵能力真正的源头关注甚少”(69 页)。阿什顿在神学上颇为敏锐;他显然对礼拜中的每一个层面都经过仔细思考——从主餐到圣公会牧师传统上所穿的礼服,无不如此。他围绕自己在克莱默著作中所观察到的三项特征来构建论述:共同敬拜应当合乎圣经、易于理解、并且保持平衡。这三点本身当然各有价值,但在我看来,它们尚不足以支撑一整套完整的敬拜神学。例如,“平衡”这一概念本身并不容易界定,阿什顿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74 页)。
此外,书中其他作者还提出了同样不可或缺的基督徒共同敬拜特征。另一个略显意外之处在于,阿什顿在这章中并未将讲道置于特别突出的地位。他关于讲道的论述本身是好的(99–100 页),但讲道在他这篇专文中的重要性,明显不如在其他作者的文章中那样突出。当然,他的一些圣公会立场也会令浸信会信徒产生不快——例如,他假定基督徒父母的孩子都是基督徒,除非能够证明他们不是(105 页)。尽管如此,阿什顿这篇专文的真正价值在于其高度的实践性。他逐一评论了礼拜中的诸多具体元素,包括音乐、祷告、戏剧、礼拜带领、公告等,并就这些环节应当如何、何时进行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在章节结尾对自己教会礼拜实践所作的自我批判。可以看出,他在思考各个环节如何彼此配合、诗歌的歌词与旋律将如何影响礼拜,甚至他个人的动作与所使用的专业术语会如何教导会众时,展现出何等细致而周全的用心。
肯特·休斯是伊利诺伊州惠顿大学教会(College Church in Wheaton)的牧师。他的专文一开始,便引用了清教徒与自由教会领袖对英国圣公会提出的一系列批评。刚读完阿什顿的文章,又注意到他对讲道着墨相对不多,此时再看到清教徒对圣公会的首要批评,就显得格外耐人寻味了。休斯写道:“这项批评的核心,在于讲道的本质。圣公会偏好《公祷书》中的讲章,而清教徒则坚持对圣经进行厚重而深入的释经”(143 页)。(公平地说,阿什顿同样致力于厚重的释经;但有趣的是,这位圣公会牧师将文章重点放在礼仪上,而这位自由教会牧师则毫不含糊地把讲道置于核心位置。)休斯还用一段颇具启发性的论述,解释了为何在非礼仪性的礼拜中,读经和较长的祷告几乎销声匿迹。随着查尔斯·芬尼(Charles Finney)等复兴主义者实践方式的流行,讲道之前的一切内容——尤其是“呼召”环节——都被视为“前奏”。因此,“为了不延长这些‘前奏’,圣经诵读被削减;同样的原因,祷告也被缩短甚至干脆省略”(148 页)。人不禁要问,这样的决定是否明智?而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休斯提出的六个基督徒敬拜特征,这也构成了他这篇专文的核心:敬拜必须以神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以圣道为中心,关乎委身于圣洁的生活,全身心的参与,并且充满敬畏。我对这些特征的批评,与我对阿什顿的评价基本一致:它们本身都很有帮助,但尤其是后三项——委身、全身心投入与敬畏——在某种程度上显得带有随意性。为什么是这三项,而不是“相关性”“传统”或“末世性”呢?因此,尽管这六个特征各自都有价值,它们仍需要本书其余内容的补充,才能避免视角上的狭隘。休斯对“把圣经读好”的重视令人耳目一新,也值得高度称赞。他在附录中收录了约翰·布兰查德(John Blanchard)的一篇默想文字,任何负责公开宣读圣经的人,都很适合将其作为早晨灵修的阅读材料(190–191 页)。此外,休斯还提到,他和教会同工会定期抽出几个小时,在惠顿学院一位演讲学教授的指导与点评下,一起练习公开读经(176 页)。这实在是一份美好的见证,彰显了休斯对神话语的敬畏与热爱。还有什么,比以最严谨、最用心的态度将圣经呈现在会众面前更重要的事呢?
提摩太·凯勒(1950-2023)曾担任纽约市救赎者长老教会的牧师。他的专文探讨了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关于共同敬拜的神学思想。除卡森的专文之外,这一篇大概是全书中最为全面的敬拜神学论述。凯勒在“敬拜之争”中辨识出两条主要思想脉络:二者都以圣经为首要根基,却从此分道扬镳。第一种是当代敬拜,它从圣经出发,然后将当代文化“接入”作为第二来源;第二种是历史性敬拜,同样始于圣经,却回溯并借鉴较早期的敬拜形式。凯勒综合这两条脉络,主张共同敬拜应当运用三种资源:圣经、传统与文化。他指出,这正是加尔文在规划教会共同敬拜时所采取的方式。
凯勒认为,改革宗的共同敬拜应当具有三项特征:表达上的简朴、目标上的超越,以及在次序上对福音的重演。其中,对“超越性”的强调尤为发人深省。在我看来,凯勒的判断是正确的: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尤其是在他所牧养的美国特定地区——人们真正渴求的是“超越与体验”,而不是许多清教传统教会中常见的“高度认知取向”的聚会,也不是“慕道友聚会”那种“轻松随意”的氛围(201 页)。当然,凯勒并非主张去迎合后现代文化,而是要吸收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如个人主义、感伤主义、理性主义)的合理批评,并将这些洞见融入共同敬拜之中。那么,如何在保持简朴的同时营造超越感?凯勒认为,这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是“说话、诵读、祷告与歌唱的品质”。他指出:“粗糙草率会立刻抽干聚集敬拜的纵向维度。”第二,则在于“带领聚集敬拜之人的仪态或内心态度”(213 页)。
凯勒这篇专文中一个极为实用的部分——尤其对正在思考如何规划共同敬拜的牧者而言——是他对本教会礼仪基本结构的说明。这一结构以“呼召—回应”为核心:神的话语得到宣告,会众作出回应。凯勒将崇拜安排为三个“循环”。第一个是“赞美循环”,始于敬拜呼召,结束于会众以颂赞诗回应。第二个是“更新循环”,始于圣经对人心的查验与更新呼召,继而进入认罪,最终以感谢上帝怜悯赦罪作为结束。最后一个是“委身循环”,从讲道开始,以会众立志按所听见的道去生活作为结束。我实在难以想象,还有比这更谨慎、更具圣经素养的礼拜规划方式。
尽管凯勒这篇专文充满宝贵的改革宗智慧,但在最后几页中却出现了一处令人费解的转向。他写道:“我们常常让非基督徒音乐家参与礼拜,他们拥有极佳的恩赐与才华。我们不会让他们独唱,但会将他们纳入合奏中”(239 页)。他的理由主要有两个层面:第一,他认为“上帝在创造中赐下的普遍恩赐,与上帝在救赎中赐下的恩赐同样属于恩典之工”,因此教会允许非基督徒将其“独特的荣耀”与恩赐带来赞美造物主,是合宜的;第二,凯勒表示,他和教会领袖“祈求聚集的敬拜本身能对他们产生影响”。我当然同意音乐才干是来自上帝的恩赐,也赞同基督徒应当为共同敬拜能触动非基督徒而祷告,但我并不认为这就自然推出:非基督徒应当带领聚集的教会。无论是为了他们自己灵魂的益处,还是为了正在敬拜的信徒,难道不是让非基督徒坐在会众中,而不是站在台上,更为合宜吗?在这一点上,肯特·休斯的实践在神学上显得更为稳妥:
音乐服事者必须视自己为在圣道上的同工,并以明白的心思和投入的心志来带领。凡在敬拜中服事的人,必须是健康的基督徒——已经认罪悔改,并在上帝的恩典中,活出与其所带领音乐相一致的生命。一个严肃的事实是:随着时间推移,会众往往会变得像那些带领他们的人一样(171 页)。
《按着圣经敬拜》必将成为任何认真思考如何以深厚的圣经与神学根基来规划教会共同敬拜的牧者的案头常备之书——翻得卷角破旧也不足为奇。它将整全圣经视角、历史意识与文化敏感性有力地结合在一起。人只能盼望,卡森有一天能将自己的专文扩展成一本完整著作。
译:DeepL/STH;校:JFX。原文刊载于九标志英文网站:Book Review: Worship by the Book, by D. A. Car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