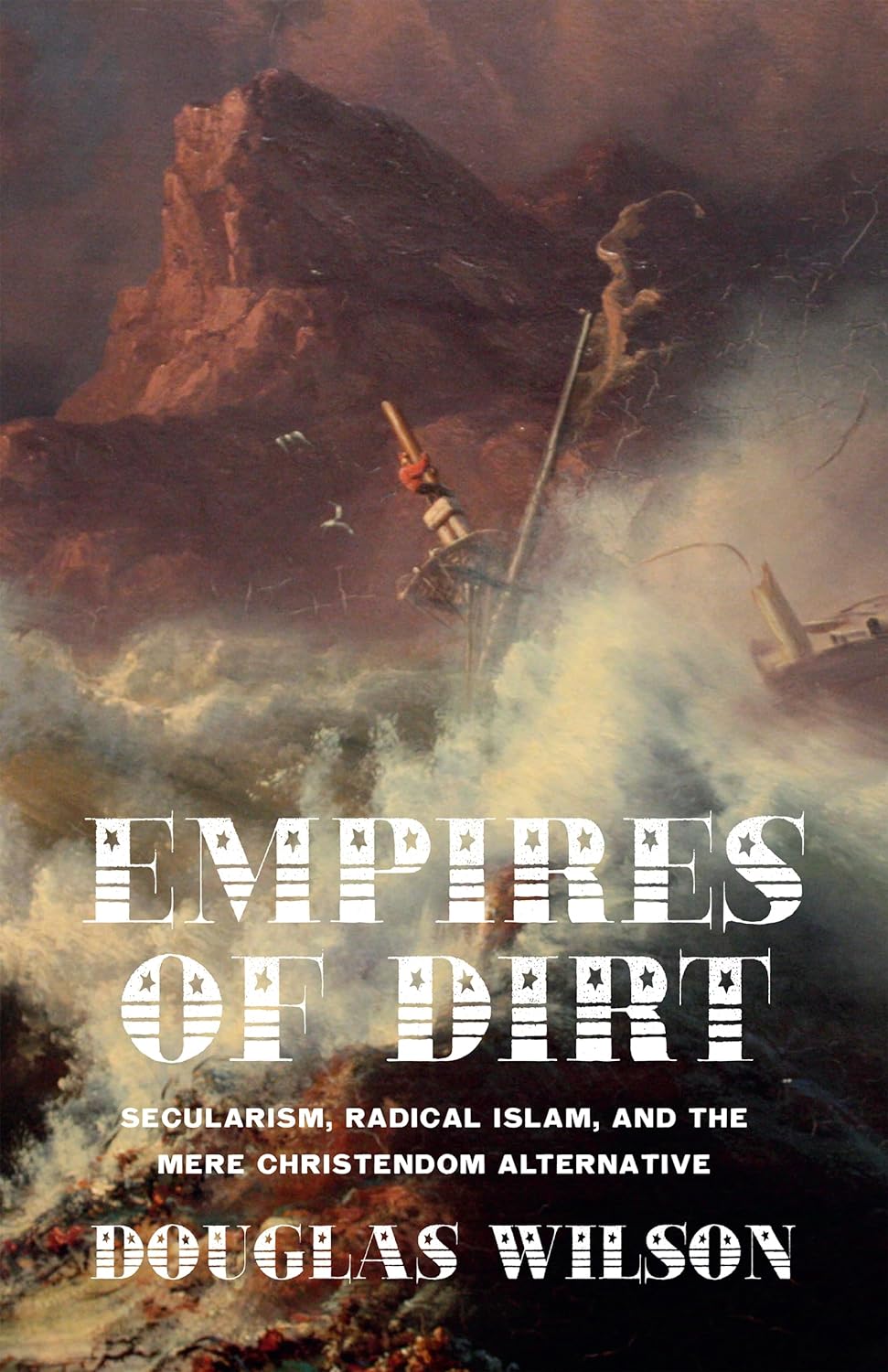
随着我们的公共论坛越来越两极化和政治化,基督教民族主义的呼声开始在心怀善意的基督徒中产生共鸣。道格·威尔逊(Doug Wilson)的《尘埃帝国》(Empires of Dirt)读起来就像一篇宣言。他的“纯粹的基督教世界”(Mere Christendom)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纯粹。
威尔逊首先提醒我们,公共领域的世俗主义并非持宗教中立态度。“软社会主义”(Soft socialism)宣扬了自己的救赎叙事。(第 8,9 页)美国犹太复国主义和美国独特论是偶像崇拜。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从来都无法令人信服地替代基督教。天然世俗主义看起来成了公共广场上唯一剩下之人,而它却让国家(显然)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公共领域神学的前景如何呢?
威尔逊首先驳斥了激进的再洗礼派(Anabaptist)政教分离论,认为它是悲观主义(豪厄瓦斯、威利蒙)以及和平主义(格雷格·博伊德)。因为“基督在捆绑撒但时已经羞辱了执政者”。(第 80 页)威尔逊说,“这应该具有明显的政治含义。”(第 81 页)其中的一个政治含义就是基督教国族主义。如果把《诗篇》第 2 篇和《启示录》19:15 的经文应用到教会上,那么就是教会用铁杖辖管,即“在这个世界上传扬和宣告上帝福音的权柄。”(第 89,90 页)当君王以嘴亲人子(the Son)时,他们会带领他们的国家——以国家的身份——拥护基督教的观点和美德,而国家则以国家民族的身份成为门徒。(第 95,259 页)
接着威尔逊驳斥甚至焚了他所谓激进两国论神学(Two-Kingdoms theology)——埃斯孔迪多(Escondido)兄弟(霍顿、范德伦、克拉克)的主张。在威尔逊看来,激进两国论完全背离了改革宗传统所具有的文化影响力。他说:“我所阅读、研究和喜爱的改革宗神学建立了一个伟大的文明。而这兄弟几个所提出的被截肢了的激进两国论改革宗神学,如果付诸实践,却连一个墨西哥卷饼摊都建不起来。”(第 145 页)威尔逊批评激进两国论这个体系是建立在“原则上与耶稣无关的文化”之上,他认为这很像流行福音派——正是后者当初曾促使了他转向改革宗神学。(第 146 页)威尔逊认为,激进两国论与“再洗礼派和复兴主义者”的关系比它与改革宗信仰的关系更为密切。
另一方面,威尔逊认为他自己与诺克斯、布策、加尔文、凯波尔和爱德华兹等一样是坚定的改革宗神学家。(第 147 页)基督是万物之王的说法意味着基督教必须有政治性,就像施洗约翰因为希律王娶了他兄弟的妻子而责备希律一样。(第120页)世上的君王必须亲吻圣子(诗 2;第 123 页)。“说这个世界的暂时性政府并非上帝的教会,并不等于说它们不应该或不需要成为基督教的。‘暂时的’和‘世俗的’这两个词并非同义词。”(第 123 页)
不过,对威尔逊来说,使万民作门徒仅仅“意味着传讲狭义的福音、拯救灵魂、建立教会、建立教会生活。”(第 125-126 页)“我相信基督教的共和党和联邦党都是通过宣教、施洗和门训建立的,而不是通过竞选、立法.......等等。”(第 157 页)。尽管如此,威尔逊的目标仍然是建立一个由基督教文化所塑造的文化。(第 121 页)“我希望生活在一个经过洗礼的文明中。这就是我所说的纯粹的基督教世界。”(第 143 页)他想要“一种具有文化影响力并能改变世界的信仰,”(第 147 页)他从但以理在巴比伦的高升和约瑟在埃及的成功看到了这个。(第 151 页)任何低于这个标准的(文化)就是模棱两可。“为世俗公共广场辩护的基督徒因此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要么这是耶稣所要的,要么就是祂不要的。”(第 155 页)
对威尔逊来说,“耶稣是万王之王……总统中的总统……祂已经是了。世界将逐渐认识到这一点,并成为基督徒,这的确是个好消息。这就是福音”,这样的真理令他振奋。(第 157 页)但这听起来很像是在说基督教世界本身就是福音,而不是福音的结果。很明显,在威尔逊论述中那不可阻挡的大规模归信和世界各国作为国家被基督教化的前景中,他的后千禧年主义占据了前沿和中心位置。
根据威尔逊的观点,“教会作为宗教实践,是正式的敬拜。天国就是围绕着教会的文化,文化从教会中生长出来。恢复教育或艺术的改革工作是天国的工作,由基督徒完成;这与由牧师、长老、执事和会众完成的教会正式工作有所不同。”(第 184 页)。不过,他建议变革的步伐要渐进,甚至要靠几代人的努力——是改革,而非革命。
在威尔逊笔下纯粹的基督教世界中,“穆斯林可以从其他国家来到这里,和平地生活……他们不能做的是争辩清真寺与教堂的钟声一样享有公共表达的权利。公共空间属于耶稣。”(第 176 页)
说到底,威尔逊“试图说服基督徒,我们会赢得这场比赛,我们应该怀着坚定的必胜之心参加比赛……我们应该现在就让基督徒知道这一点——他们不必现在就做到这些。”(第 195 页)并且“就像个人需要认识上帝一样社会也需要认识上帝……当(基督徒)在他们的国家职位上向社会宣告耶稣基督时,合乎圣经的转变过程就开启了……耶稣说要为万民施洗。耶稣说要使万民作祂的门徒。若非如此你认为祂的意思还能是什么?”(第 259 页)
这听起来像是用一种有阳刚之力的信仰替代一种阴柔的信仰。问题在于威尔逊所说的“纯粹的基督教世界”是什么意思:“我所说的‘纯粹的基督教世界’是指一个由许多国家组成的网络,这些国家通过正式、公开、全民承认的方式宣告耶稣基督的统治地位和《使徒信经》的基本真理。”(第 9 页)简单的论证就是“宗教不可能中立。因此,一方面纯粹的基督教世界与宗派林立的基督教世界形成了对比,另一方面它也和完全的世俗主义形成了鲜明对比。”(第 9 页)事实上,在威尔逊看来,“纯粹的基督教世界......同时为美国独特性和激进伊斯兰主义都提供了唯一真正的解药。”(第 28 页,参见第 47 页)
值得称赞的是,他的观点非常明确。“我主张建立一个基督教美国.........(而且)在宪法中列出耶稣基督的统治权......这个开端会让我很高兴。”(第 160 页)“(立法者)应该提出一项由《使徒信经》文本组成的宪法修正案。”(第 193 页)“我只是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领导人、法官、诗人、小丑以及全体人民——都必须承认耶稣是主。他们必须承认只有耶稣是主。其他国家也应这样做,当他们这样做时,他们当然会承认彼此是基督里的姐妹国家”(第 33 页)。他说,当然......
一些福音派人士往往对这种言论大加赞赏。但是,“纯粹的基督教世界”——修改国家宪法等——真的是最好的前进方式吗?虽然这一切都依赖于福音的推广,但是基督徒真的应该期待威尔逊所保证的那种成功吗?基督徒是否应该像威尔逊那样,将这种成功等同于福音本身?我认为威尔逊的观点所带来的问题比他所解决的问题还要多。
例如,那么如何看待挪亚之约(创 9:1-7)中的普遍恩典呢——在挪亚之约中在三位一体上帝作为万物的创造者和维系者之下的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共享空间。上帝与挪亚的盟约是保护性的,而不是救赎性的。它与所有受造物立约,而不仅仅是上帝的子民,甚至不仅仅是人类。它的标记是常见的彩虹。它划定了婚姻、生育、食物供应和惩罚性正义,惩罚性正义即国家监督的领域,向作为创造者和维系者的三位一体之上帝负责。
这种与造物主的神圣盟约一直持续到末日。因此,新约并没有废除挪亚之约。相反,挪亚之约是救赎性的生活、前进和存在的时空环境。
挪亚之约的空间是普遍恩典的空间。它既是全人类不分宗教所共享的共同空间,也是宗教之外的共同空间。它是世俗的、俗世的——不是邪恶或污秽的,但它也不是圣洁的——因为它不是因得赎而奉献的。然而,它也是恩典的,因为它推迟了最终审判,为救赎创造了时间和空间,而且它是由上帝提供的,因此所有受益者,无论是否得到救赎,都要对上帝负责。
挪亚之约的框架是神学之伞,因为它不仅包含了上帝的救赎计划,还包含了上帝对仍未信主之世人的忍耐,正如大卫·范德伦(David VanDrunen)和梅雷迪斯·克莱恩(Meredith Kline)(《天国前传》[Kingdom Prologue],第 153-160 页)、斯图亚特·罗宾逊(Stuart Robinson)(《教会是福音的基本要素》[The Church as an Essential Element of the Gospel],第 84-88 页)、赫尔曼·巴文克(Herman Bavinck)(《改革宗教义学》[Reformed Dogmatics],3 章 216-222 页)和赫尔曼·维茨乌斯(Herman Witsius)(《圣约的体制》[Economy of the Covenants],2 章 239-242 页)所认为的那样。换句话说,我们基督徒可以根据上帝之约与非基督徒共享公共空间,同时不放弃我们的信仰。耶稣是万有的君王,但祂以不同方式统治,为了不同的目的。一个是作为创造-维系者,另一个是作为救赎-拯救者。耶稣在统治……即便基督徒没有在统治。
威尔逊对挪亚之约框架的不屑带来了维系与救赎、普遍与圣洁之间的混淆。梅雷迪斯·克莱恩正是在这一点上发现了神治论脉搏上的不规则心跳,“他们未能理解圣经中关于普遍恩典文化的概念”。(天国前传》,第 157 页)。这种疏忽导致了神治论的违和;它跳过了一个节拍。
违和之处在于,按照这种说法耶稣所救赎出的只是上帝应许会暂时存留之物——普遍或公民领域。然而,洪水、所多玛和蛾摩拉,以及《约书亚记》和《士师记》中上帝命令他们彻底毁灭征服之地的人,都预示了这一领域的毁灭——不信世界所有普遍恩典的终结(路 17:26-29;彼后 2:5-9, 3:8-13)。巴比伦的灭亡和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对取代巴比伦(启 18)预示了这一领域的毁灭。
正是在这里,神治论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律法主义——要求教会做耶稣没有要求、教会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事。由于不存在公认的共同领域,《尘埃帝国》将大使命理解为教会必须对国家进行门徒训练,这就意味着要他们将政府基督教化。(第 95 页)用威尔逊的话——“‘但你们希望政府明确遵行基督教?’你完全理解了我们的立场”。(第 121 页)
然而,《使徒行传》中接受教导和受洗的只有来自不同国家和种族的个人,而绝非国家本身。约翰在《启示录》5:9 中的说法证实了这一点:你“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启示录》7:9 也是如此)祂没有赎回许多国家。祂从各国中赎回了一个新的国际性族群。“在他们的国家职位上”(第 259 页,强调为原文作者所加)向社会传讲福音根本不是耶稣委托教会做的事。
正是因为忽略了普遍恩典的空间,神治论才会错误解读基督教国家的身份。彼得认为世上的基督徒就像流亡巴比伦的以色列人(彼前 1:1, 2:11)。更重要的是,彼得将从万国出来的教会本身称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族类(e;qnoj a[gion)、属神的子民(lao,j)——而不是现代的民族国家或这个国家中从教会而出的文化(第 184 页;参启 1:6, 5:10)。在一个普通的国家(common nation)中教会本身应该成为圣洁的族类(holy nation )——即在一个非基督教的国家中,教会在基督里向神负责,不是根据神与祂子民所立的新约,而是根据神与所有受造物所立的挪亚之约。当基督徒忽略了普遍恩典时,他们就会产生出为国家施洗的冲动,而不是改革教会。
威尔逊批评了亨特(J.D. Hunter)对《耶利米书》29:4-7 “忠心地参与”的观点(第 150-151 页),认为他轻视了《但以理书》6:23-28 节的文化逆转和胜利。但神给巴比伦流亡者的建议是“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耶 29:4-7)在上帝给流亡者的建议中,明显没有任何将巴比伦改建成新耶路撒冷的命令。以色列的流亡者在巴比伦的福祉中找到了他们的福祉,而不是反过来。更重要的是,上帝命令他们在巴比伦建造和种植,虽然祂知道在七十年后,祂将摧毁这座他们在其中寻求福祉的城市。
在威尔逊看来,“教会要把世界变成世界应该成为的样子”。(第 183 页)这就是我不认同后千禧年论之处。这并不是说基督徒不能或不应该对文化产生影响。而是说这种影响只是福音的一种副产品,是维系性和暂时性的,而不是基督徒救赎性的目标,不会产生永恒的结果,更不是福音本身。(第 157 页)我们不应该因此而悲观丧气或与世隔绝。我们仍然要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方面为圣经中的公义和仁慈而共同努力。我们仍在建设和栽种,但我们是作为盐、作为暂时的防腐剂来做这些。这些工作即便只是暂时性的,也是重要的;哪怕不是救赎性的,也仍然重要。
这一点在教牧上带来的关注是,许多新加尔文主义(neo-Calvinist )的凯伯尔主义者(Kuyperians)把范德伦(VanDrunen)所谓的“末世的负担”放在了文化变革上,而无论在圣经中还是在改革宗神学中都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负担。[1] 我们在世上的职业工作是我们在挪亚之约中所承担的一部分责任——暂时性、维系性的工作;而不是永恒、救赎性、天国的工作(反对 Wilson,第 149-150 页)。我们传福音、门训和建立教会是我们在新约中的一部分责任——救赎性的工作,真正的天国的工作。混淆这些区别会使人从暂时的职业中寻求永恒的意义,从而导致幻想破灭。更重要的是,它给什么算为传福音带来了混淆。
流亡者生活在巴比伦中可能会给个别的巴比伦人带来救恩,但不是对巴比伦这个国家的救赎。但以理在所流放之国高升也并没有给巴比伦带来“救赎”,就像约瑟也未能“救赎”埃及一样。事实上,上帝就是通过审判这些征服了祂圣洁子民的普通国家而救赎了祂的子民。上帝仍在摧毁巴比伦及其所代表的悖逆的世界。(启示录18:1-24)威尔逊通过约瑟和但以理的例子论证说,我们将赢得文化战争。(第 151-153 页)然而在巴比伦,除了灵魂,我们什么也赢得不了。
诚然,随着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基督徒,可能会有更多的人自愿投票赞成修改宪法。但这似乎也更像是基督教化的民主民粹主义。对于那些家园被巴沙尔·阿萨德炸毁的叙利亚基督徒,或生活在伊斯兰教法下的中东基督徒来说,这将是难以接受的。耶稣必须把世界变成它应该成为的样子。当祂这样做时,祂将完成亚当未能完成的事情。这就是信心所相信的。这并非“是不信将这些事情的成就置于历史进程之外”(第 194 页),而是一种恒久忍耐的盼望,无论表象如何。
《尘埃帝国》假定了一种先验主义末世论。对《新约》末世论的另一种解读则更有解释力,它认为巴比伦(与上帝及其子民对立的世界)正在日益强大(提后 3:13;启 12-17)。与此同时,教会也在不断强大。冲突会时起时伏,最终会达到高潮,直到耶稣再来摧毁巴比伦、拯救教会并使万物焕然一新。[2]
因此,《启示录》第 18 章中上帝对巴比伦的毁灭,预示着上帝在末世对这个与基督对立之世界的审判,并表明了基督徒不应该更新这个世界。我们寻求天国;我们看见、服事并进入天国;但我们不会用教会外的、改变文化的方式,使用我们现在拥有的原材料来建造它。巴比伦不是给基督徒修复或更新的,新耶路撒冷会替代它。
威尔逊在其他地方申明:“实现大使命......需要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基督教世界。”[3] 威尔逊在本书中所呼吁的是“‘接受过洗礼的文明’……这就是我所说的‘纯粹的基督教世界’”。(第 143 页)。然而,他所假定的那种洗礼是反常的。2017 年,威尔逊放弃了“联邦愿景”(Federal Vision)一词,但他并没有放弃他自己曾以这一名称冠名的神学。“这一声明代表了我改变了对自己信仰的称呼。但它并不代表我信仰的内容有任何实质性的转变或改变……我仍然确认我在“联邦愿景”中签字确认的所有内容。”[4]
我们不能在这里重新讨论整个“联邦愿景”,但威尔逊仍然申明:“所有受洗归入三位一体之名的人都在基督的盟约生活中与基督联合,因此从这个恩典的立场上跌落的那些人确实是从恩典中跌落了......背道者不能仅靠着外在的标志与基督相连。”[5] 他还确认“上帝通过洗礼使人归入三位一体的圣名,从而正式地将人与基督及其新约的子民联合起来。”[6] 等一下,洗礼使你与基督结合?这难道不是天主教的圣礼主义(sacramentalism)吗?[7]
解释一下,如果威尔逊的“纯粹的基督教世界”要想对你起作用——他把它定义为“受洗的文明”(第 143 页)——你就必须要接受洗礼在某种程度上是作为一种国族化的圣礼,它以某种方式使人与基督结合,但洗礼后的罪会妨碍它,而且唯有洗礼后的顺服才能最终成就它。威尔逊说他的“纯粹的基督教世界”是非宗派性的,但他将洗礼视为国家化圣礼的观点却是宗派性的——对于一个自诩为威斯敏斯特清教徒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灵活的举动。
当然,“纯粹的基督教世界“并不是当今后千禧年论的唯一品牌;不买此一版本后千禧年论的账,你仍然可以成为后千禧年主义者。但是,“纯粹的基督教世界”似乎是联邦政府的“联邦愿景”,因此它是一种应该被抵制的后千禧年论。在这种观点中,只有一个恩典之约(没有行为之约,但基督的顺服仍然归入信徒名下),一个国家所有人民都要在肉体上接受洗礼,领受一种不一定能得救的拣选;加入《马太福音》19:28 的普遍重生,但这种重生仍可能在你身上死;进入与基督的属灵结合,但这种结合仍有可能破裂。你受洗的祝福取决于你受洗后的顺服。这看起来就像是超级挂名基督徒盟约——靠恩典进入,靠行为留下。
威尔逊说“我想生活在受洗的文明中”。(第 143 页)我也想。但我们都得等到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那一天,因为只有到那时,它才像为新郎装饰好的新妇,并且“凡不洁净的……总不得进那城”。(启 21:27)。这才是真正接受了洗礼的文明。但只有耶稣才能带来它。赞美上帝,祂会的。
* * * * *
[1] David VanDrunen, Natural Law and the Two Kingdoms: A Study in the Development of Reformed Social Thought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10), 349-350, 367.
[2] 参照William Hendriksen, More than Conquerors (Grand Rapids: Baker, 1940, 1967, repr. 2015).
[3] 《联合联邦愿景》("Joint Federal Vision Statement")中的《下一个基督教世界》("The Next Christendom") https://federal-vision.com/ecclesiology/joint-federal-vision-statement/
[4] 《不再联邦愿景》("Federal Vision No Mas")https://dougwils.com/s16-theology/federal-vision-no-mas.html
[5] 《联合联邦愿景》("Joint Federal Vision Statement" )https://federal-vision.com/ecclesiology/joint-federal-vision-statement/
[6] 同上
[7] 威尔逊在其他地方明确肯定了唯独因信称义。在此,我们以善意揣测他,他愿意按照婴儿洗礼派的主张,肯定某些人(比如婴孩)可以与基督联合,进入圣约之中,可以被称为“基督徒”,但这只是一种客观性标识,而非主观性标识。换句话说,他认为教会就像古代以色列一样,是一个按蓝图设计的混合群体,而浸信会则不同,他们认为教会总是渴望完全重生,“在基督里”就是指客观和主观地在基督里。问题是,这样的语言在最好的情况下仍然会起到混淆视听的作用,有可能与他所肯定的“唯一真实”(sola fide)相矛盾,在最好的情况下仍然会带来大行其道的挂名基督徒,“教会”并不比追求其他神灵的古代以色列更健康。
译:DeepL;校:Jenny。原文刊载于九标志英文网站:Book Review: Empires of Dirt, by Douglas Wil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