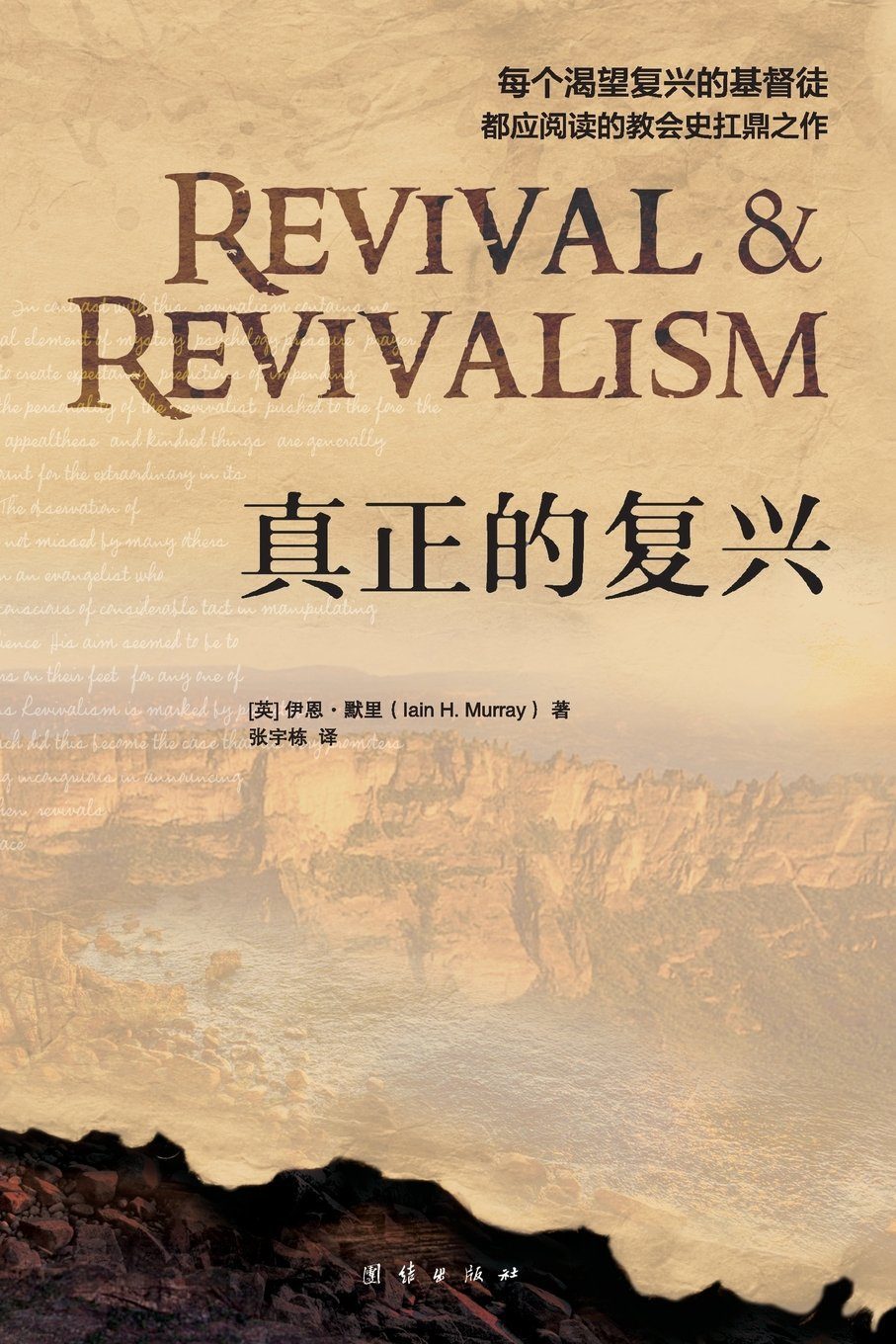
“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是一个永远都合适问自己的问题,且往往具有启发性。然而,当代福音派并没有以应该的姿态经常问自己这个问题。
伊恩·默里在他的著作《真正的复兴》(Revival and Revivalism: The Making and Marring of American Evangelicalism, 1750-1858,中译本由团结出版社 2012 年出版)中讲述了一个故事,该故事有助于解释福音派——浸信会,长老会,卫理公会等——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书名概括性地讲述了整个故事。在默里研究的 109 年,也就是 1750 到 1858 年间,美国福音派对福音的理解和经验如何从“复兴”变成了“复兴主义”。
背景:第一次大觉醒
并不是说 1750 年之前发生的事情不重要。大约从 1735 年到 1740 年,因着约拿单·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乔治·怀特腓(George Whitefield)等人的讲道,美洲殖民地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灵性振兴,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大觉醒。这一现象是由他们的讲道所推动的,这种讲道强调神的圣洁,罪的严重性,人被罪奴役,以及需要圣灵使人重生,人才能悔改、相信和得救。
虽然对这种讲道的肤浅回应会不可避免地与真实的回应混在一起,但与这些事件同时代的人认为它们是真正的复兴。他们相信这场属灵运动是由神的主权所决定的,神将他的灵以奥秘而不寻常的方式浇灌下来,从而使寻常的、合乎圣经规定的传福音途径结出了不同寻常的果实。
爱德华兹和怀特腓的属灵后裔
于是,默里的故事从第一次大觉醒的属灵后裔开始说起,当中有撒母耳·戴维斯(Samuel Davies)和亚历山大·麦克沃特(Alexander McWhorter),他们在新英格兰到弗吉尼亚的各处服事(1-4 章)。这些牧师持守的神学正是促使爱德华兹和怀特腓传道的神学,并且他们自己也受到过1735-1740年间那些事件的影响。在整个 18 世纪下半叶,这些人和跟从他们的服事者定期经历神对他们事工的祝福,祝福的方式也完全可以称为“复兴”。
复兴:神的恩赐,并非必然发生
这些牧师像他们的前辈一样,知道复兴是神主权的作为,不能用任何其他方式来解释。因此,他们传讲福音,恳求罪人与神和好,并年复一年地为结果子祷告;而神有时惊人地祝福这些工作,有时却不会,其中的原因唯独他自己知道。
换句话说,这些复兴既不是人所筹划的,也不是人所实现的。它们不涉及任何不寻常或新奇的传道技巧。因此,它们被认为是神的恩赐。
然后,从 1800 年左右起,复兴开始在这个年轻的国家大规模爆发,从东北部到西部的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而真正惊人的是,这种大规模的复兴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持续了约 30 年,理所当然地被称为第二次大觉醒。
第二次大觉醒
一开始,人们对这次复兴的理解与之前的复兴相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神学和实践上开始出现转变,到复兴结束时相当于发生了一场革命。(关于这部分故事,请参阅第 5 到 12 章。)
例如,1800 年在肯塔基州的肯里奇市,长老会的户外“圣餐季(communion seasons)”(遵循苏格兰的传统做法)成为了导火线,它所引发的事看起来像是圣灵的一次重大运动。这些聚会迅速地发展。来自卫理公会等其他宗派的牧师也参与了讲道。大量不参加任何教会的人不远千里前来听道。许多人对讲道和唱诗做出回应,回应的方式有时候混乱而激烈。
最终,这些聚会的领袖在如何应对聚会中出现的过度情绪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一些人(大多数是长老会的)认为应该根据情况允许或斥责这些表现,而其他人(卫理公会)则倾向于将所有这些表现都视为神的灵工作的明证。
从此,肯塔基这次事工中的卫理公会领袖采取了一种策略,该策略原本是对复兴的回应——即,长期户外聚会——并将其作为他们实现复兴的工作中的关键部分。此外,这些卫理公会的领袖和其他一些人,基于一种完全不同的归信教义,开始把他们的工作专注在诱导人对福音有外在、直接的回应。
两个重大转变
和这个故事类似的事情也在其他地方发生。到 19 世纪 20 和 30 年代,整个美国福音派发生了两个重大转变。
第一个是归信教义的转变。直到 1800 年,福音派几乎都相信并传讲,神必须主权性地赐给某人新的本性,使他或她能够悔改和相信。到 19 世纪 30 年代,另一种对归信的理解广泛地取代了这种观点,这种理解认为,悔改和相信完全取决于一个人自己的能力。
这导致(或者说:在某些情况下,随之而来的是)传福音做法上的转变。许多福音派采取的做法是,要人立刻做决志。“决志专座”、讲台呼召、在公祷中单独提名祷告,警告听众立刻回应以免失去悔改的机会——所有这些以及更多的做法都源于这样一种新的信念,即一个人有能力归信,甚至能影响他人归信。
结果:复兴主义
这两个转变的结果是,教会领袖开始将复兴视为可以通过使用适当的方法来确保发生的事情——任何会引发立刻决志或决志外在表现的方法,都叫“适当的”。查尔斯·芬尼(Charles Finney)大力提倡这种理解,但到第二次大觉醒结束时,它已经成为大多数美国福音派的共识。历史学家威廉·麦克罗林(William McLoughlin)甚至说,到 19 世纪中叶,这种新的体系已成为美国的国教(277 页)。
于是,复兴主义诞生了。可以肯定的是,复兴主义是在真正复兴的土壤中长起来的。但这种复兴主义的新做法与以前对复兴的理解截然不同,并很快取而代之。“复兴”成为了旨在促进复兴的聚会的代名词。与前几代人不同,1830 年后的福音派可以说获得了一种提前几个月就能把复兴排进日程的能力。
这种复兴的目标是确保尽可能多的人能立刻做归向基督的决志祷告。因此,在福音派的知觉中,似乎不再能意识到虚假归信的可能性。很少有人问他们的新举措是否会产生出和真正的门徒一样多的假信徒。
无需多说,不难看出我们是如何从 19 世纪 30 年代的复兴理念变成今天许多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传福音做法的。无论我们想的是体育场中进行的奋兴会,还是试图每周日都重现这种氛围的教会,都是这样。
然而,正如默里在本书最后一章正确地指出,这种复兴主义和支持它的神学,表明严重偏离了合乎圣经的归信教义和传福音做法。因此,《真正的复兴》应当激励我们批判性地仔细反思我们的教会和我们的传福音做法。
为此,以下是该书带来的七条教训,对牧师们来说应该有特别的意义。
第一,不要把外在的某个行为与内心改变混为一谈。
关于讲台呼召的起源,默里这样写道:
起初,没有人宣称它是一种归信的途径。但很快,也是不可避免地,回应讲坛呼召与归信就混为一谈了。人们听到讲员恳求他们到前面来,就像恳求他们悔改和相信一样迫切。(186 页;另见 366 页)
一个人穿过大堂,走到讲台面前做一个“决志”,并做出任何其他行为,却没有归信,这是可能的。而没有采取任何这些特定的外在步骤却真的归信了,也是有可能的(不过,归信当然总是会以可见的果子表现出来)。
因此,牧师不应该把任何外在行为当成归信一样来谈论。他们应当警惕那些似乎将二者等同起来的传福音技巧。
第二,谨防产生虚假归信者。
当然,有些最初认信的人后来证明没有悔改,这是不可避免的,但牧师的传福音方式可以把虚假归信减到最低,也可以增加。例如,默里引用撒母耳·米勒(Samuel Miller)的话说,“决志专座”(讲台呼召的前身)的设立促进了“肤浅、无知、未受训的认信者的快速倍增”——即,虚假的归信者(366 页)。
第三,对于立刻给得救确据的做法要谨慎。
正如《新罕布什尔信仰告白》(New Hampshire Confession)所说,坚忍是真基督徒的重要标志(来 3:6、14)。信心通过果子来表明自己——无论是好是坏,是真是假(太 7:15-27)。然而默里指出,复兴主义的新方法实际上建立在决志后立刻应许得救确据的基础之上。
但用决志专座传福音的人,想要消除那些公开回应之人心中的一切疑虑。它的全部吸引力……在于它暗示:只要做出一次回应,就能确保得救。如果承认了回应公开的呼召与归信之间没有确定的联系,就会破坏整个体系。(368 页)
换句话说,新方法的整个要点就在于,回应保证得救。在此基础上,只要人们在礼拜结束时到前面来,讲道人就会立刻且毫无保留地向他们保证会得救。
最幼小和软弱的基督徒也有可能获得得救确据,但这确据应该始终以基督客观的工作为基础,并由生命转变后结出的果子来证实。
所以,牧师们,对于立刻给得救确据的做法要谨慎。而且要注意别在错误的基础上给出确据。
第四,将你的事工紧紧连于神话语中的要求。
在默里的叙述中,从某种程度上说关键的转折点是,19 世纪早期的卫理公会将某些新奇的、圣经以外的做法——长时间的户外营地聚会,让人立刻做决志的技巧等——视为产生归信的关键(184 页)。
当然,基督徒可以自由地使用圣经中没有直接提到的方式来传福音。如果保罗能租下推喇奴学房(徒 19:9),那么现代福音派为什么不能在体育场里传福音呢?
但问题在于,这些新方法成了硬性要求。它们成了灵丹妙药。它们成了必要条件,人们无法想象缺少了这些还有人能得救。
相反,要把你的信心放在神已经要求你做的事情上——传讲神的道。相信神已经在他的道里面给了你成为忠心牧师所需的一切。使用他给你的工具做工,并相信他必使你的工作结出果子。
第五,要确保是神学驱动你的实践,而不是相反。
浸信会在 19 世纪早期几乎是清一色的改革宗救恩论,但讲台呼召的做法在他们当中蔓延开来之后,默里这样写到(325-326页),
这种做法并没有像 19 世纪 30 年代的大多数教会那样被接受,但毫无疑问,对于浸信会来说,正是所谓新式布道的成功,促使她更快地采用了它,并逐渐改变其教义为它辩护。
在这种情况下,实践的屁股决定了神学的脑袋。新式布道的逻辑进入了他们的神学体系并改写了DNA。不知不常见中,大量的浸信会采用了一种传福音方法,这种方法不仅与他们的神学信念相抵触,而且最终破坏了它们。
第六,不要将外在的成功等同于神的认可。
据默里所记,在新旧势力的冲突中,复兴主义者经常打出外在成功这张王牌(282 页)。正如一位同时代牧师的名言,“在神赐福时永远不要批评。”
以成功为论据的第一个问题是,“成功”并不总是成功。默里写道,“毋庸置疑的是,把‘归信’当成是即时、公开的决志,并立即在宗教媒体上公布可确定的数字,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重复‘成功’的表象。”
但这些“决志”中有多少代表了真正的归信呢?有多少人受洗,加入教会并开始了新的生活?如果当时的数字和今天用类似方法产生的数字相符的话,那么答案可能是“不多”。
以成功为论据的第二个问题是,神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祝福我们,不管我们自身的状况如何。每次神使用牧师的讲道使人归信时,他都是在祝福那人的工作,不管他有没有罪错。那么你怎么能确定神是因为某种新方法而祝福一个事工,而不是无所谓有没有它呢?
当然,我们应该期待神祝福那些合乎他的道的传讲和做法。但我们不能把他的工作简化为“最忠心”=“最蒙福”的机械模式。我们也不能从表面上的成功去倒推什么是正确的神学和做法。
第七,赞美常规的做法。
默里写道,上一代的牧师将复兴视为神的恩赐,“旧派的人虽然像他们一样热切相信复兴……然而他们找不到因处于常态而沮丧的圣经理由”(385 页)。这些人知道,大多数时候,事工是缓慢而单调的工作。他们知道“这人撒种,那人收割”的道理。他们“相信神会以合适的方式赐下祝福——无论是高昂的形式……还是以安静的方式”(385 页)。
因此,最后,不要因缓慢成熟的果子而感到气馁。相反,要依靠神通过常规的蒙恩途径工作。赞美常态。
正如我希望这篇书评所证明的那样,《真正的复兴》一书已经成为一部经典之作,理由有很多。这本书很长,内容密集,还有些杂乱无章;但读完它所花的时间和精力会得到超额的回报。我向所有在职的和立志成为教会领袖者、以及任何爱问“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这个问题的基督徒,推荐这本书。
译校:无声宏扬。原文刊载于九标志英文网站:Book Review: Revival and Revivalism: The Making and Marring of American Evangelicalism, 1750-1858, by Iain Murr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