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想探讨的是十七世纪中叶特殊(或加尔文主义)浸信会起源的时代……他们决心不惜代价,在上帝有明确命令之处顺服上帝;他们认识到,苦难是上帝用来使我们成圣的一种手段。他们还意识到,为基督的缘故受苦是他们荣耀伟大救主的一种方式。出于所有这些原因,他们会把迫害甚至殉道视为给教会的礼物。
我想探讨的是十七世纪中叶特殊(或加尔文主义)浸信会起源的时代……他们决心不惜代价,在上帝有明确命令之处顺服上帝;他们认识到,苦难是上帝用来使我们成圣的一种手段。他们还意识到,为基督的缘故受苦是他们荣耀伟大救主的一种方式。出于所有这些原因,他们会把迫害甚至殉道视为给教会的礼物。 与任何环境下的福音工作一样,南非既有令人振奋之事,也有令人沮丧的事情。作者试通过三个方面的概述来描绘这幅图画:教会成员制和教会纪律的实践、领袖的职责以及神话语的地位。作为一个新的民主国家,南非仍然在长期受压迫的历史中挣扎……通过对我们国内趋势的简要回顾也提醒我们,主的国度确实也正在这里建立。
与任何环境下的福音工作一样,南非既有令人振奋之事,也有令人沮丧的事情。作者试通过三个方面的概述来描绘这幅图画:教会成员制和教会纪律的实践、领袖的职责以及神话语的地位。作为一个新的民主国家,南非仍然在长期受压迫的历史中挣扎……通过对我们国内趋势的简要回顾也提醒我们,主的国度确实也正在这里建立。 因此,一位对神治论和重建派持关切态度的浸信会牧师至少应致力智慧地做这三件事:第一,他研究神治论和重建派的承诺和结果,以确保能准确、诚实地与这一立场进行互动。浸信会期刊是一个很好的起点。第二,他明确阐述浸信会圣约神学以及如何应用它来恰当地区分律法和福音的含义。最后,敬畏主超过一切,他在必要时以温和和耐心的态度纠正神治论和重建派的错误——这都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和祂羊群的益处。
因此,一位对神治论和重建派持关切态度的浸信会牧师至少应致力智慧地做这三件事:第一,他研究神治论和重建派的承诺和结果,以确保能准确、诚实地与这一立场进行互动。浸信会期刊是一个很好的起点。第二,他明确阐述浸信会圣约神学以及如何应用它来恰当地区分律法和福音的含义。最后,敬畏主超过一切,他在必要时以温和和耐心的态度纠正神治论和重建派的错误——这都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和祂羊群的益处。 最近出版的一本名为《联会》(Association)的著作从圣经、神学和历史角度,为教会有意识地合作提供了令人振奋的理由。该书还列举了一些实际例子,说明这种合作在今天可以是什么样子。
最近出版的一本名为《联会》(Association)的著作从圣经、神学和历史角度,为教会有意识地合作提供了令人振奋的理由。该书还列举了一些实际例子,说明这种合作在今天可以是什么样子。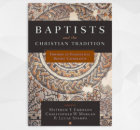 作者介绍了《浸信会与基督教传统》一书,该书强调了研习神学和传承伟大传统的益处——为了坚固浸信会的信仰。它将使读者接触到重要的历史资料,推动我们更深入地接触传统,看到基督教信仰中一直存在的长线。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盼望神学检索把我们引回我们唯一的权威来源——圣经。
作者介绍了《浸信会与基督教传统》一书,该书强调了研习神学和传承伟大传统的益处——为了坚固浸信会的信仰。它将使读者接触到重要的历史资料,推动我们更深入地接触传统,看到基督教信仰中一直存在的长线。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盼望神学检索把我们引回我们唯一的权威来源——圣经。 作者作为一位圣公会的牧师,从四个方面总结了浸信会教会体制给他带来的有益的提醒。感谢基督,我们不是因宗派得救,而是因基督得救。健康的教会大公性——即合一,植根于我们对福音的共同信心——这意味着圣公会、浸信会、长老会等之间可以享受团契。即使存在差异,我们也能相互砥砺。
作者作为一位圣公会的牧师,从四个方面总结了浸信会教会体制给他带来的有益的提醒。感谢基督,我们不是因宗派得救,而是因基督得救。健康的教会大公性——即合一,植根于我们对福音的共同信心——这意味着圣公会、浸信会、长老会等之间可以享受团契。即使存在差异,我们也能相互砥砺。 作者作为一位浸信会牧师,列举了五个他从长老会牧师、教师和思想家身上所学到的宝贵经验。这并不是说我不能从浸信会的思想家那里学到这些东西,也不是说我没有从浸信会弟兄姊妹的教导和著作中学到很多东西。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我所遇到的长老会牧师、教师和作家的影响,无论是通过亲身经历还是通过他们的著作,我的生活、思想和事工都会差得多。
作者作为一位浸信会牧师,列举了五个他从长老会牧师、教师和思想家身上所学到的宝贵经验。这并不是说我不能从浸信会的思想家那里学到这些东西,也不是说我没有从浸信会弟兄姊妹的教导和著作中学到很多东西。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我所遇到的长老会牧师、教师和作家的影响,无论是通过亲身经历还是通过他们的著作,我的生活、思想和事工都会差得多。 牧师们需要了解,在19世纪,美国浸信会发生了改变。这一改变塑造了我们对归信、成员资格、洗礼和实践“重生教会成员资格”的意义这些事情的直觉。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斥着复兴主义的直觉和制度化实践的世界,这些无意中所破坏的,甚至是浸信会的立会之本。通过了解复兴主义历史根源,牧师们将更有能力去批判性地评估今天常常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做法。
牧师们需要了解,在19世纪,美国浸信会发生了改变。这一改变塑造了我们对归信、成员资格、洗礼和实践“重生教会成员资格”的意义这些事情的直觉。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斥着复兴主义的直觉和制度化实践的世界,这些无意中所破坏的,甚至是浸信会的立会之本。通过了解复兴主义历史根源,牧师们将更有能力去批判性地评估今天常常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做法。